懂视生活2024年11月12日发布:许春华 孔子诗学思想的两种面向——《论语》与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的比较
⭐发布日期:2024年11月12日 | 来源:懂视生活
【2024正版资料大全】 |
【2024年正版资料免费大全公开】 |
【新奥天天免费资料大全】 | 【资料大全正版资料】 | 【新澳门三肖中特期期准】 | 【新澳好彩资料免费提供】 | 【2024新澳最精准资料】 | 【澳门正版资料大全免费网】 | 【新澳门精准全年资料免费】 | 【2024年新奥门管家婆资料先峰】 |
| 【新澳门精准免费资料大全】 | 【2024澳门天天彩免费正版资料】 | 【新澳精准资料免费大全】 | 【新澳好彩免费资料查询最新版本下载安装】 | 【2024年澳门最新版本】 | 【2024资料精准大全】 | 【新澳门天天开奖资料大全】 | 【新奥天天免费资料大全正版优势】 |
贵州省孔学堂发展基金会资助
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、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来源期刊
本文来源:《孔学堂》(中英双语)2022年第4期。
摘要:《论语》与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关于孔子对《诗》《乐》所做工作的记述,显示出孔子诗学思想的两种不同面向:第一,从《诗》之结构看,《论语》“兴观群怨”是对人生意义的全副涵盖,《孔子世家》“四始说”突出了人伦之道与政治教化。第二,从“乐”之功能看,《论语》侧重于涵养君子的道德人格与审美人格,《孔子世家》着重于维系天下的政治秩序与伦理秩序。第三,从孔子师生之间论诗的对话看,《论语》是对《诗》的哲学阐释,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思想特质;《孔子世家》突出了孔子为天下修道的使命感与担当精神,其政治哲学倾向非常明显。两种文本中,孔子诗学思想的不同面向,是理解孔子儒学与汉代儒学不同旨趣的诗学维度。
关键词:孔子诗学 《论语》 《孔子世家》 面向
作者许春华,哲学博士,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访问学者。
大纲一二三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(以下简称《孔子世家》)是记述孔子事迹的正史,也是我们了解孔子思想的重要文献。其中孔子对《诗》《乐》所做的工作,亦有大量的记述。按照相近、类似的原则,笔者将这些记述分为三种,第一种是专门对《诗》所做的工作,第二种是专门对《乐》所做的工作,第三种是孔子与不同弟子就同一首诗的对话。把《孔子世家》这些记述与《论语》的相关文本进行比较,就会发现它们其中一部分是来自《论语》的原有文本,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在《论语》中出现。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:如何看待《论语》与《孔子世家》这些相同或不同的文本?如何判定它们在孔子诗学思想中的地位?这些文本虽然都指向了孔子诗学思想,但它们是相同性质的孔子诗学思想,还是孔子诗学思想的不同面向?带着这些问题,本文梳理、解读《孔子世家》里的这些文本,并与《论语》中相关文本进行比较,以期更加客观地把握孔子诗学思想的不同面向,在理解孔子儒学与汉代儒学不同思想旨趣上,增添一种新的诗学维度。
一
我们先看《孔子世家》记述孔子对《诗》所做的工作:
古者《诗》三千余篇,及至孔子,去其重,取可施于礼义,上采契、后稷,中述殷、周之盛,至幽、厉之缺,始于衽席,故曰“《关雎》之乱,以为《风》始,《鹿鸣》为《小雅》始,《文王》为《大雅》始,《清庙》为《颂》始。”……礼乐自此可得而述,以备王道,成六艺。
…………
孔子以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教,弟子盖三千焉,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。
春秋时代贵族教育的教学体系中,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已成为主要的组成部分。[1]孔子承袭了春秋时代的诗教传统,亦以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为主要教学内容,教授其弟子、其子,故其弟子能够“通六艺”者,亦即成绩优秀、突出者72人。
不过,如果仅仅止于此,那么孔子与春秋时代的其他思想者并无分别。孔子之所以能够在先秦诸子“哲学的突破”中,成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,与其对《诗》所做的工作有直接关联。依照上文,孔子的工作及其思想贡献,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。
1.“去其重”。《诗》为何会出现“重”即重复的情况,至少有以下两种原因。第一,《诗》最初的文本形态并非一种固定的写本,而是口耳相传的话本,“在早期文明时代,在书写文本出现之前,会有一个长时期的口述传统,在口述话本中某些言说是被作为权威性的东西来传述的”[2]。亦即是说,在孔子时代,《诗》并不存在一种标准写本,而是在流传广布的过程中,存在多种多样的话本,[3]这极有可能导致孔子看到的《诗》,篇章或字词重复者较多。第二,夏、商、周三代采诗之官负责采风、收集,“天子五年一巡守。岁二月东巡守……命太师陈风以观民风”(《礼记·王制》)。《孔子世家》记述孔子“上采契、后稷,中述殷、周之盛,至幽、厉之缺”,跨越数个朝代的采风、收集,如果没有做认真、细致的整理工作,那么《诗》之重复叠加就在所难免。所以,孔子对《诗》所做的第一项工作,就是整理、编撰,删减其重复者。[4]《诗》之定本300余篇由此而传。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:“孔子闵(悯)王路废而邪道兴,于是论次《诗》《书》,修起《礼》《乐》。”“论次”即编排,“修起”即整理,这是从另一角度谈论孔子所做的“去其重”,“闵(悯)”说出了孔子所做《诗》之工作的一种精神,正因为孔子对三代王道的向往,秉持一颗悲悯天下之心,才有孔子对《诗》不厌其烦“去其重”,才成就了承载中国哲学与文化传统的“六艺(六经)”。
2.“取可施于礼义”。在孔子对《诗》所做的工作中,这一项最为关键。“取”即选拣、择取;“施”即赋予、阐释,即赋予、阐释《诗》一种新的意义,这种意义的标准即“礼义”。“礼义”并非“礼”与“义”二者相加,而是指“礼”之“义”,孔子曰:“君子义以为质,礼以行之……君子哉。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程子云:“此四句只是一事,以义为本。”[5]这种“礼义”含有双重向度,可指向“礼”之内在义,即“礼”的内在精神;或“礼”之根本义,即“礼”的价值依据。亦可二者兼具。
春秋时代,《诗》成为承载贵族阶层思想观念的载体,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七年》载赵衰推荐郤縠之语:“说《礼》《乐》而敦《诗》《书》。《诗》《书》,义之府也;《礼》《乐》,德之则也。”“义”即正当,是指《诗》《书》已经含有贵族阶层的政治活动、社会活动的价值依据,“《诗》《书》作为精神和价值的根据体现在贵族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之中,支撑并塑造着这个时代”[6]。这种价值依据并非《诗》之语言形态,而是《诗》之文本承载的道德观念,其中“礼”是最核心的价值观念。[7]孔子对《诗》所做的主要工作,即“《诗》《书》执礼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。“执”,秉持、笃行。孔子所云《诗》之“礼”与春秋时代之“礼”有其本质不同,正在于“仁”的发明。上文所云“礼义”,即“礼”之“义”,执礼、行礼的正当性,即在于“仁”。“仁”既为“礼”之内在精神,亦为“礼”之本质规定,诚如孔子云:“人而不仁,如礼何。”(《论语·八佾》)《诗》→“礼(义)”→“仁”,这一思想进路,使孔子诗学获得了“仁”之内在精神与本质规定,这才是孔子诗学与春秋时代诗学传统的根本不同。
3.“四始说”排列了《诗》之结构。对《诗》的编撰、排列、选取,无疑会涉及《诗》之结构问题。按照《孔子世家》所载,孔子所做工作之一即确认了“四始”,“《关雎》之乱,以为《风》始,《鹿鸣》为《小雅》始,《文王》为《大雅》始,《清庙》为《颂》始”。《史记正义》云:“乱,理也。”[8]这种“四始说”并未出现在《论语》孔子诗学文献中,这是我们比较《论语》与《孔子世家》诗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《论语》中孔子在给弟子教《诗》、与弟子论《诗》时,亦谈到了一种结构,“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。《诗》,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。迩之事父,远之事君。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(《论语·阳货》)。这是按照孔子诗学内在的思想逻辑,排列出的一种思想结构,“兴”与“观”是指《诗》能够兴起、发现一个道德精神的意义世界;“群”与“怨”是指《诗》承载的道德教化与社会教化;“事父”与“事君”是人伦之道的代表,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是指《诗》对万物的认知。朱熹云:“学《诗》之法,此章尽之。”[9]此章既是孔子对《诗》之思想结构的确立,亦是对孔子儒学人生意义与价值的全副涵盖。
按照《孔子世家》所载,“四始说”是孔子确认的一种《诗》之结构。不过,这种排列顺序并非孔子发明,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吴公子季札观鲁乐,鲁国乐工演唱《诗》的次序,先《风》中的《周南》《召南》《邶》《鄘》《卫》《王》《郑》《齐》《豳》《唐》《陈》《桧》,然后是《小雅》《大雅》,最后是《颂》。[10]这种结构顺序,恰恰也就是《孔子世家》记述的结构顺序,可谓《诗》的一种功能结构。新出土文献《孔子诗论》作为孔门后学的诗学文本,第四支简和第五支简所论《诗》之结构,也是“《邦风》”“《小夏(雅)》”“《颂》”的排列顺序。[11]这说明孔子时代,《诗》之《风》《雅》《颂》的功能结构顺序当已基本成型。[12]所以,我们以“确认”一语来界定《孔子世家》中《风》《雅》《颂》的功能结构,以与《论语》中,孔子对“兴观群怨”思想结构的“确立”相区别。
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,就会发现《孔子世家》的“四始说”与《论语》中“兴观群怨”的思想意涵也有异同。《孔子世家》的“四始说”,突出了儒家的人伦之道,明确把《诗》引向了政治教化与道德教化,这是汉代儒家诗学思想最为重要的特征。《关雎》为《风》之首篇,《毛诗序》作为汉代儒家诗学思想传统的奠基者,开篇即说:“《关雎》,后妃之德也。风之始也,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。”[13]在汉儒看来,夫妇之道为人伦之道的根基,故引《关雎》阐释为夫妇之道。“风”即教化,“风以动之,教以化之”[14]。按照这一思想逻辑,《大雅》《小雅》《颂》的首篇,亦承载着儒家伦常之道,钱穆先生对汉儒这种思想旨趣一目了然,“故《诗》始《关雎》,夫妇之际,人道之大伦也。此说《风》始《关雎》之义,甚为明当。盖《清庙》《文王》,所以明天人之际,定君臣之分也,《小雅·鹿鸣》,所以通上下之情。而《风》之《关雎》,则所以正闺房之内,立人道之大伦也。周公之所以治天下,其道可谓毕具于是矣”[15]。
从《论语》“兴观群怨”的思想意涵来看,与《孔子世家》“四始说”有相同之处,但相异之处才是根本。《论语》“兴观群怨”结构亦非常重视《诗》所承载的人伦之道与道德教化,文中的“可以群”“可以怨”,朱熹注:“和而不流。怨而不怒。”[16]可见“群”“怨”并非仅仅是情感的表达,而是以一种中和之德加以调适,以实现《诗》之教化功能;文中提到的“事父”与“事君”,是孔门儒家人伦之道的基点。[17]与《孔子世家》不同,《论语》中孔子把“事父”与“事君”视为儒家人伦之道的代表,朱熹注:“人伦之道,《诗》无不备,二者举重而言。”[18]进一步说,这种人伦之道与道德教化,第一,从形式结构来说,排列在“可以兴”“可以观”之后;第二,从思想意涵来说,“可以兴”是指《诗》可以兴发一种“善意”,[19]“可以观”是说学《诗》、论《诗》可以发现一个道德精神世界,而人伦之道与道德教化,是从内心“善意”、道德精神转换而出。这种人伦之道与道德教化,是《诗》的一种内在目的,是内心“善意”、道德精神的自然转化与外在展现,二者的关系可谓由“体”发“用”,由“用”显“体”。《孔子世家》的“四始说”强调人伦之道与政治教化,是为了《诗》能够发挥维系汉代统治者的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的作用,但是汉儒对《诗》之意义的这种阐释,导致孔子诗学的思想旨趣发生了根本变化。相对于《论语》中孔子诗学来说,这种变化或者可以说是《诗》的一种“异化”,“本来,社会的关怀与此世伦常价值的体现乃是诗的内在本质之彰显,此时,这却变成了外在于诗的目的,诗成了达成社会控制的手段。《诗》的社会性一旦由内在的目的异化成外在的目的……诗歌异化成伦理规范,甚至变成了法规教材”[20]。这种思想旨趣的不同,才是《论语》“兴观群怨”与《孔子世家》“四始说”的本质差异。
4.“礼乐可得而述,以备王道,成六艺。”如前所述,《诗》《礼》《乐》已经成为周人贵族教育的教学内容,也是周人维系天下的文明形态。其中《礼》主要是一种仪式形态,《乐》则是一种音舞形态,《诗》则是一种语言形态。以一种语言表达方式,来表达内在的情感、心志,《诗》弥补了《礼》《乐》文明形态的不足。“王道”作为孔门儒家的一种政治理想,不仅需要“礼”“乐”文明形态的支撑,亦需要《诗》这种文明形态的维系。《诗》《礼》《乐》共存、互渗的文明形态,才可谓王道“完备”的文明形态。最后“成六艺”,孔子之“成”,第一,是“六艺”之形成,没有孔子对“六艺”所做的编撰、笔削、阐释、转化,中国哲学传统与文化传统的“六艺(六经)”不可能彻底完成。第二,是“六艺”之完备,即孟子所谓“集大成”,“孔子之谓集大成,集大成也者,金声而玉振之也”(《孟子·万章下》)。作为孔门后学的出土文献《郭店楚墓竹简》,多次完整地谈论“六艺(六经)”及其思想主张,如《六德》:“观诸《诗》《书》则亦在矣,观诸《礼》《乐》则亦在矣,观诸《易》《春秋》则亦在矣。”[21]《语丛一》:“《诗》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,《书》者所以会□□□□者也,《礼》所以会□□□□也,《乐》所以会□□□□也,《易》所以会天道人道也,《春秋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。”[22]孔门儒家对“六艺”所做的工作,“说明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这‘六种’文本在东周时代已‘基本’统一和定型”[23]。所以,司马迁在《孔子世家》另一处称颂孔子:“孔子布衣,传十余世,学者宗之。自天子王侯,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,可谓至圣矣!”“折中,正也。”“折中于夫子”,即孔子成为删削、阐释“六艺”的权威,由此可谓“至圣”。
二
我们再看《孔子世家》关于孔子对“乐”所做工作的记述,文本摘录是按照《孔子世家》的前后顺序。
孔子……与齐太师语乐,闻《韶》音,学之,三月不知肉味,齐人称之。
孔子击磐。有荷蒉而过门者,曰:“有心哉,击磐乎!硁硁乎,莫己知也夫而已矣。”
孔子学鼓琴师襄子,十日不进。师襄子曰:“可以益矣。”孔子曰:“丘已习其曲矣,未得其数也。”有间,曰:“已习其数,可以益矣。”孔子曰:“丘未得其志也。”有间,曰:“已习其志,可以益矣。”孔子曰:“丘未得其为人也。”有间,(曰)有所穆然深思焉,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。曰:“丘得其为人,黯然而黑,几然而长,眼如望羊,如王四国,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。”师襄子辟席再拜,曰:“师盖云文王操也。”
孔子语鲁大师:“乐其可知也。始作翕如,纵之纯如,皦如,绎如也,以成。”吾自卫反鲁,然后乐正,《雅》《颂》各得其所。
三百五篇,孔子皆弦歌之,以求合《韶》《武》《雅》《颂》之音。
“弦歌”是孔子生活世界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,“子之武城,闻弦歌之声”(《论语·阳货》)。学《诗》诵读即“弦歌”,孔子教授弟子学《诗》,同时也诵读之,《诗》与《乐》在孔子儒学中得到了统一。“三百五篇,孔子皆弦歌之,以求合《韶》《武》《雅》《颂》之音。”《韶》即舜帝之乐,《武》即武王之乐,孔子及其弟子颂《诗》成“乐”,其标准是“合《韶》《武》《雅》《颂》之音”。孔子在肯定《诗》之《雅》《颂》承载的礼乐精神的同时,亦对当时的雅乐《韶》《武》给予了价值判定。结合《论语》中“乐”之文献,我们逐次进行探讨。
孔子对《韶》乐、《武》乐的评判。《论语·述而》:“子在齐闻《韶》,三月不知肉味,曰: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。”《孔子世家》记述稍有不同,但是两个关键点相同,“闻”乐、“三月不知肉味”。孔子以“闻”而非日常之“听”或“观”,足见《韶》乐美德之“味”浓郁,以致孔子感叹“为乐之至”。第一,“闻”说明孔子并非欣赏《韶》乐的艺术形态与表现手法,而是对《韶》乐承载的盛美、盛德的由衷赞叹,以“闻”对应《韶》乐之“味”。此“味”并非物质性之“味道”,而是精神性之“意味”,“三月不知肉味”是“闻乐”的精神感受。第二,“子谓《韶》,‘尽美矣,又尽善也’。谓《武》,‘尽美矣,未尽善也’。”(《论语·八佾》)这是孔子唯一一处对《韶》乐、《武》乐的共同判定。“尽美”为《武》乐与《韶》乐共同之处,“尽善”与“未尽善”则为二者之分野。“尽”亦即“至”“极”,孔子赞赏《韶》乐,正是因为其“美”之“至”与“善”之“至”,即内在的道德精神与审美精神的统一。二者相较而言,孔子更为突出“尽善”之道德精神,《礼记·乐记》云:“仁近于乐。”徐复观认为:“孔子的所谓‘尽善’,只能指仁的精神而言。因此,孔子所要求于‘乐’的,是美与仁的统一;而孔子之所以特别重视‘乐’,也正因为在‘仁’中有‘乐’,在‘乐’中有‘仁’的缘故。”[24]第三,由“闻”而固守《韶》乐之“尽美”亦“尽善”之精神,以致“乐正”之“正己”。“闻”犹孔子所云“朝闻道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之“闻”,朱子释“闻道”,“若是知得真实,必能信之笃,守之固”[25]。所谓“信之笃”,即真诚信持;所谓“守之固”,即自觉坚守。第四,是由“闻”将《韶》乐之“尽美”亦“尽善”精神推己及人,“故乐非独以自乐也,又以乐人;非独以自正也,又以正人。大矣哉!为此乐者,不图为乐至于此”[26]。《韶》乐不仅可“正己”“正人”,亦可安宁天下,“乐则《韶》舞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即孔子所云“为邦”之道。“乐之至”,莫不“至于斯”也。
孔子对《雅》《颂》的评判。孔子回到鲁国,最为重要的一项使命即“乐正”。“子曰:‘吾自卫反鲁,然后乐正,《雅》《颂》各得其所。’”(《论语·子罕》)一些注解者围绕孔子是“正”《诗》或者“正”“音”,乐律之“正”抑或音律之“正”,争执不休。这种探讨仅仅是在春秋时代诗学传统中就《雅》《颂》而论“乐正”,并未在《论语》孔子诗学视域中来探究“乐正”之义。“各得其所”之“所”,亦即“乐”之“正”的另一种表达方式,清人刘宝楠云:“是乐各有所真,有不如是而必不可者,所谓正也。”[27]何谓“不如是而必不可者”,刘氏并未明确。《论语》之“正”,多指涵摄道德精神的品格、行为或为政之道,如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;其不正,虽令不从”(《论语·子路》)。“政者,正也。子帅以正,孰敢不正?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所以,《论语》“乐正”主要指“正”之本然义,即《雅》《颂》之“乐正”。“子语鲁大师乐,曰:‘乐其可知也:始作,翕如也;从之,纯如也,皦如也,绎如也,以成。’”(《论语·八佾》)《孔子世家》述此文于孔子返鲁之后,亦即“《雅》《颂》各得其所”之事,故此章“乐其可知”乃“言乐正而后可知也”[28]。体现于“翕如”“纯如”“皦如”“绎如”即乐之始终,“翕如”,起合变动;“纯如”,纯和如一;“皦如”,清浊明别;“绎如”,畅茂条达;“以成”即指合乐之“正”。
《孔子世家》对“乐正”的记述,与《论语》没有区别。不过,若结合《史记》其他文献,则可看出《孔子世家》更侧重于《雅》《颂》之社会教化、政治教化功能。《史记·乐书》云:“天子诸侯听钟磬未尝离于庭,卿大夫听琴瑟之音未尝离于前,所以养行义而防淫佚也。夫淫佚生于无礼,故圣王使耳闻《雅》《颂》之音,目视威仪之礼。”《雅》《颂》既以庄重肃穆的仪节规范贵族的言行举止、仪容体态,亦以和谐、愉悦的音声感发人心、调适情感,养护仁义精神。《史记·乐书》又云:“天子躬于明堂临观,而万民咸涤荡邪秽,斟酌饱满,以饰厥性,故云《雅》《颂》之音理而民正。”“雅”,“正”也;“理”,条理、节律。汉儒所谓“理”,不仅指“乐”之理,也指天下的秩序;“雅”,不仅指“乐”之雅,更为主要的是指“正天下也”[29]。在汉儒看来,“乐正”即天下“正”,《雅》《颂》“各得其所”,意味着百姓各安其位,天下秩序良好。
《孔子世家》所载“孔子学鼓琴师襄子”,《论语》中并无相应文本。这段文本以师襄子与孔子的对话为主线,表达学“乐”的境界可以递次升进(“益矣”),是一个由“习其曲”“习其数”“习其志”,最后“得其为人”的历程。“习其曲”即了解“乐”的内容,“习其数”即掌握“乐”的方法,“习其志”即体悟“乐”的境界。这种境界即“穆然深思”“怡然高望”,“穆然”即庄重之貌,“深思”指“乐”使人省思、沉思;“怡然”即愉悦之态,“高望”指“乐”使人高瞩远望。“得其为人”即学“乐”的最终目的,“黯然而黑,几然而长,眼如望羊,如王四国”,是孔子对文王作为“乐”之作者的判定,这种判定是孔子通过“闻”其音、“听”其声,达到与文王内心的相融而至。[30]
为何司马迁把“孔子学鼓琴师襄子”这段文本安排于此,学界无明确定论。文本以文王操琴结尾,并非仅仅因为文王喜欢鼓琴,而是以文王象征圣贤“如王四国”即一种以“王道”怀天下之心。孔子对文王此种境界心领神会,故师襄子惊讶而拜。《孔子世家》把《论语·宪问》“孔子击磬”章,安排于此文之前,可谓独具匠心。《论语》原文与《孔子世家》有所不同,“子击磬于卫。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,曰:‘有心哉!击磬乎!’既而曰:‘鄙哉!硁硁乎!莫己知也,斯已而已矣。深则厉,浅则揭。’子曰:‘果哉!末之难矣’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。隐士以“深则厉,浅则揭”(《卫风·匏有苦叶》)之诗,讥讽孔子不知深浅,是因为不理解孔子与文王一样,存有一种济世救人的仁者情怀,朱熹注:“圣人之心未尝忘天下,此人闻其磬声而知之。”“圣人心同天地,视天下犹一家,中国犹一人,不能一日忘也。”[31]这种文本的前后安排,体现出汉儒思想的连贯性。
三
孔子与弟子对话论《诗》,是阐发孔子诗学思想的主要路径。《论语》中以孔子与子夏、子贡的对话比较典型。
子夏问曰:“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,素以为绚兮。”何谓也?子曰:“绘事后素。”曰:“礼后乎?”子曰:“起予者商也!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。”(《论语·八佾》)
子贡曰:“贫而无谄,富而无骄,何如?”子曰:“可也,未若贫而乐,富而好礼者也。”子贡曰:“《诗》云:‘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’,其斯之谓与?”子曰:“赐也,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,告诸往而知来者。”(《论语·学而》)
子夏所云“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”出自《卫风·硕人》,是对卫夫人庄姜的赞美之诗。子贡所云“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”出自《卫风·淇奥》,是说玉石切磋琢磨的工夫。这种对话,体现着《论语》中孔子论《诗》的特点。第一,孔子师生对话,是对《诗》之意义亦即儒家道德精神的一种自觉召唤。按照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理路,“意义”就是阐释者之“前理解”对文本价值取向的内在规定。[32]孔子对《诗》之文本的删订、编撰、选取,亦即把“礼义”作为“前理解”植入《诗》之文本的过程。孔子与子夏对话,孔子以“素”为“后”,子夏则以“礼”为“后”,孔安国传:“以素为礼。”[33]子夏以“素”喻“礼”,颇为契合《诗》之道德精神。孔子与子贡对话,从“贫而无谄,富而无骄”,转换到“贫而乐,富而好礼者”,意味着一种道德升进的工夫。第二,孔子师生对话是多重阐释主体共同完成的。如果我们把这种论《诗》的对话,看作对《诗》之意义世界的一种阐释,那么阐释主体并非单指孔子,亦非仅指弟子,参与阐释文本意义的,还应该包括《诗》之文本。单一的孔子、弟子、《诗》之文本,都不能构成对《诗》自足、自洽的“诠释单元”,应秉持一种哲学诠释学的“文本意义论”。[34]只有对话情境中的孔子、弟子、文本相互启发,才会激发孔子儒学思想世界的创构。第三,孔子师生对话是一种“共同理解”。孔子最后赞誉子夏、子贡“始可与言《诗》矣”,意味着这种对话是孔子师生对《诗》之意义的“共同理解”。这种“共同理解”不是对《诗》之“原义”的机械复制,也不是对《诗》之技巧、手法的描述;不是孔子对其弟子的一种灌输式、认知式的“传授”,也不是在一方慑于“权威”,对另一方默许的“理解”。这种“共同理解”是师生双方相互兴发、相互分享的理解,是孔子与其弟子论题视域不断切换,即不断“扬弃”的过程,亦是对《诗》之意义重新认识的过程,这种重新认识就是对《诗》的“创造性”行为,是对《诗》之意义逐步推进的“理解”过程。第四,孔子师生对话是相互兴发的过程。孔子肯定子夏“起予者商也”,朱熹注:“起予,言能起发我之志意。……所谓起予,则亦相长之义也”[35]。“起”虽然由孔子发出,但它并非单向度的,而是“相长”即孔子与子夏的相互启发;所谓“志意”并非一般的志意,而是对“礼后”的一种理论期许。孔子肯定子贡“告诸往而知来者”,“告”“知”并非日常活动的告诉、知道,子贡引《诗》证成了孔子儒学思想,“子贡闻一知二,故能告往知来”[36]。“告诸往而知来者”这种阐释方法,从时间维度上打开了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相互交织的无限可能,《诗》之阐释不仅指向过去的历史经验,亦指向未来的维度,从而开启了无限可能的阐释意义。
《孔子世家》亦记述孔子与其弟子子路、子贡、颜回论《诗》的对话:
孔子知弟子有愠心,乃召子路而问曰:“《诗》云:‘匪兕匪虎,率彼旷野。’吾道非邪?吾何为于此?”子路曰:“意者吾未仁邪?人之不我信也。意者吾未知邪?人之不我行也。”孔子曰:“有是乎!由,譬使仁者而必信,安有伯夷、叔齐?使知者而必行,安有王子比干?”
子路出,子贡入见。孔子曰:“赐,《诗》云:‘匪兕匪虎,率彼旷野。’吾道非邪?吾何为于此?”子贡曰:“夫子之道至大也,故天下莫能容夫子。夫子盖少贬焉?”孔子曰:“赐,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,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。君子能修其道,纲而纪之,统而理之,而不能为容。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。赐,而志不远矣!”
子贡出,颜回入见。孔子曰:“回,《诗》云:‘匪兕匪虎,率彼旷野。’吾道非邪?吾何为于此?”颜回曰:“夫子之道至大,故天下莫能容。虽然,夫子推而行之,不容何病,不容然后见君子!夫道之不修也,是吾丑也。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,是有国者之丑也。不容何病,不容然后见君子!”孔子欣然而笑曰:“有是哉颜氏之子!使尔多财,吾为尔宰。”
这三段文本的特点,是孔子与不同弟子,均围绕同一首诗进行问答。“匪兕匪虎,率彼旷野”出自《小雅·何草不黄》,原意是指并非兕也非虎这类野兽,但仍旧穿行于旷野,疲于奔命。孔子引此诗文,是诘问三位弟子,自己的学说并非兕、虎这类猛兽,可为何不能大行其道,反而是周游列国不得志。子路的回答是,孔子“仁”“智”的主张还没有达到最高层次,所以人们不会信从、实践;孔子则以伯夷、叔齐、比干这些“仁者”“智者”为例,说明仁者未必令人信从,智者亦未必让人践行。子贡回答说,孔子之道过于宏大,以至于天下不能容纳,孔子应该降低标准;孔子则反诘,君子修道,以为天下纲纪、统理,不修道却追求为天下所容,这种志向非君子所为。颜渊的回答是,为天下修道,是我们的责任,而修道却不被认可,是当权者的丑陋之处;天下不容并不影响对道德理想的追求,矢志不渝方显君子本色。三段文本呈现出三位杰出弟子的不同思想形象,相比而言,最后颜渊的回答,深得孔子之意,体现出“君子修道立德,不为穷困而败节”(《孔子家语·在厄》)的使命与担当,和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的志向与勇气。
从《论语》与《孔子世家》孔子师生论《诗》对话来看,《论语》是对《诗》的哲学阐释,揭示了《诗》之儒学意义,《诗》融入了孔子思想体系;《诗》亦激发了孔子儒学的道德精神,《诗》之阐释赋予孔子儒学一种鲜明的诗性色彩,透显出一种人文主义思想特质。《孔子世家》中孔子师生对话,《诗》仅仅是作为问答的引子,这种一问一答的方式,并没有《论语》中那种孔子与弟子之间循循善诱、互相兴发的过程,也就没有起到共同理解儒家思想的作用。这种对话突出了孔子为天下修道的使命感与担当精神,孔子的圣人化、权威性非常明显,孔子与弟子间的师生等级关系,取代了《论语》那种平等主体之间的探讨,这与汉代儒学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,极力抬高孔子地位的政治哲学倾向不无关系。《论语》与《孔子世家》的相关文本,显示出孔子诗学思想的不同面向,这为我们理解孔子儒学与汉代儒学的不同思想旨趣,增添了一种新的诗学维度。
[1] 《国语·楚语上》载,楚庄王使士亹傅太子箴,士亹就世子教育请教于申叔,申叔答曰:“教之《春秋》,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,以戒劝其心;教之《世》,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,以休惧其动;教之《诗》,而为之导广显德,以耀明其志;教之《礼》,使知上下之则;教之《乐》,以疏其秽而镇其浮;教之《令》,使访物官;教之《语》,使明其德,而知先王之务,用明德于民也;教之《故志》,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;教之《训典》,使知族类,行比义焉。”参见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:《国语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8年,第528页。申叔所云这九种教学科目,并未涉及到儒家“六艺”中的《易》。
[2] 陈来:《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》,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09年,第215页。
[3] 在出土的楚大师编钟上,有《诗》的铭文,可与《诗》之定本对应。如“慎淑温恭”与“淑慎尔止”(《大雅·抑》)、“武于戎功”与“念兹戎功”(《周颂·烈文》)、“龢鸣且皇”与“喤喤厥声,肃雍和鸣”(《周颂·有瞽》)对读。参见付林鹏:《周代的文化认同与文学交流——以音乐制作、语言传译为中心》,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20年第5期。这说明《诗》在口耳相传过程中,会发生个别字、词的异变,甚至篇章的改变。
[4] 司马迁所说的这种删减重复的工作,在秦汉时期并非个案,汉代刘向奉命整理皇家所藏《荀子》传本,“所校雠中《孙卿书》凡三百二十二篇,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,定著三十二篇,皆以定杀青简,书可缮写”。参见刘向:《荀子叙录》,转引自王先谦:《荀子集解》,沈啸寰、王星贤点校,北京:中华书局,1988年,第557页。刘向所做的主要工作,即是将《荀子》由原来的322篇删减为定本32篇。
[5] 朱熹: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3年,第165页。
[6] 王博:《中国儒学史·先秦卷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1年,第37页。
[7] 徐复观认为,春秋时代是一个以“礼”为中心的人文世纪。“礼”由西周初期偏重于“仪”的意义,转化为春秋时代的道德观念。参见徐复观:《中国人性论史》,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1年,第29—31页。
[8] 张守节:《史记正义》,司马迁:《史记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2年,第1937页。
[9] 朱熹: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第178页。
[10] 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季札观乐:吴公子札来聘。……请观于周乐。使工为之歌《周南》《召南》,曰:“美哉!始基之矣,犹未也,然勤而不怨矣。”为之歌《邶》《鄘》《卫》,曰:“美哉,渊乎!忧而不困者也。吾闻卫康叔、武公之德如是,是其《卫风》乎?”为之歌《王》,曰:“美哉!思而不惧,其周之东乎!”为之歌《郑》,曰:“美哉!其细已甚,民弗堪也。是其先亡乎!”为之歌《齐》,曰:“美哉,泱泱乎!大风也哉!表东海者,其大公乎!国未可量也。”为之歌《豳》,曰:“美哉,荡乎!乐而不淫,其周公之东乎?”为之歌《秦》,曰:“此之谓夏声。夫能夏则大,大之至也,其周之旧乎?”为之歌《魏》,曰:“美哉,沨沨乎!大而婉,险而易行,以德辅此,则明主也!”为之歌《唐》,曰:“思深哉!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?不然,何忧之远也。非令德之后,谁能若是?”为之歌《陈》,曰:“国无主,其能久乎?”自《桧》以下无讥焉!为之歌《小雅》,曰:“美哉!思而不贰,怨而不言,其周德之衰乎?犹有先王之遗民焉!”为之歌《大雅》,曰:“广哉!熙熙乎!曲而有直体,其文王之德乎?”为之歌《颂》,曰:“至矣哉!直而不倨,曲而不屈,迩而不逼,远而不携,迁而不淫,复而不厌,哀而不愁,乐而不荒,用而不匮,广而不宣,施而不费,取而不贪,处而不底,行而不流。五声和,八风平;节有度,守有序。盛德之所同也。见舞《象箾》《南籥》者,曰:“美哉,犹有憾!”见舞《大武》者,曰:“美哉,周之盛也,其若此乎?”见舞《韶濩》者,曰:“圣人之弘也,而犹有惭德,圣人之难也!”见舞《大夏》者,曰:“美哉!勤而不德。非禹,其谁能修之!”见舞《韶箾》者,曰:“德至矣哉!大矣!如天之无不帱也,如地之无不载也!虽甚盛德,其蔑以加于此矣。观止矣!若有他乐,吾不敢请已!”参见杨伯峻:《春秋左传注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90年,第1161—1165页。
[11] 《孔子诗论》第四支简和第五支简的简文:“诗丌(其)猷坪(平)门,与()(贱)民而()之,丌(其)甬(用)心也(将)何如?曰:《邦风》是也。民之有戚患也,上下之不和者,其用心也将何如?曰:《小夏(雅)》是也。有成功者何如?曰:《颂》是也。”参见马承源主编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一)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年,第130页。
[12] 参见王中江:《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1年,第346—348页。另外,作为《孔子诗论》与《孔子世家》之间的文献,《荀子·儒效》所载与《毛诗序》所论,也是依据《风》《小雅》《大雅》《颂》的顺序。
[13] 毛亨传,郑玄笺:《毛诗传笺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18年,第1页。
[14] 毛亨传,郑玄笺:《毛诗传笺》,第1页。
[15] 钱穆:《读〈诗经〉》,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(一)》,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09年,第118页。
[16] 朱熹: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第178页。
[17] 《论语》中孔子的儒学重视君臣关系、父子关系在人伦纲常中的根本地位,孔子“正名”说:“君君,臣臣,父父,子子。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《论语》中孔子诗学强调“事父”与“事君”,类似的语句见于子夏之言,“事父母,能竭其力;事君,能致其身”(《论语·学而》)。汉代儒家强调夫妇之道在人伦纲常中的根本地位,故《毛诗序》阐释《诗》之首篇《关雎》:“后妃之德也。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。”“先王是以经夫妇,成孝敬,厚人伦,美教化,移风俗。”汉代儒家这种诗学思想,或许受到了《易》的影响,《周易·序卦传》:“有天地然后有万物,有万物然后有男女。有男女然后有夫妇,有夫妇然后有父子,有父子然后有君臣,有君臣然后有上下。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。夫妇之道,不可以不久也,故受之以《恒》,恒者,久也。”恐怕这也可以解释,为何《诗》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六艺略”中排列地位下降到第三位,而《易》则上升为首位的缘由。《史记·外戚世家》明确把“《易》基《乾》《坤》,《诗》始《关雎》”连在一起。王博认为:“儒家最初似乎最重视君臣和父子,如《论语·微子》中子路所谓的‘大伦’主要指这两者。而且在《论语》中,并没有涉及到夫妇的关系。但在郭店中,夫妇一伦的重要性被突出了。所以很多篇经常把君臣、父子和夫妇相提并论,这些被认为是每个人一定要面对的关系。”参见王博:《中国儒学史·先秦卷》,第258页。王博所云确是。但从“五伦”之首要地位来说,《论语》更重父子和君臣关系,《易传》和《毛诗序》更重夫妇之道。
[18] 朱熹: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第178页。
[19] 程子云:“夫子言‘兴于《诗》’,观其言,是兴起人善意,汪洋浩大,皆是此意。”参见程颢、程颐: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二,《二程集》,王孝鱼点校,北京:中华书局,2004年,第41页。
[20] 杨儒宾编:《导言》,《中国经典诠释传统(三):文学与道家经典篇》,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8年,第7页。
[21] 《简帛书法选》编辑组编:《郭店楚墓竹简·六德》,北京:文物出版社,2003年,第49页。
[22] 《简帛书法选》编辑组编:《郭店楚墓竹简·语丛一》,第58页。此文参见廖名春:《郭店楚简引〈书〉论〈书〉考》,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:《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,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2000年,第123页。
[23] 王中江:《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》,第326页。
[24] 徐复观:《中国艺术精神》,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1年,第9页。
[25] 黎靖德编:《朱子语类》卷二十六,王星贤点校,北京:中华书局,1986年,第660页。
[26] 程树德:《论语集释》,程俊英、蒋见元点校,北京:中华书局,1990年,第457—458页。
[27] 刘宝楠:《论语正义》,高流水点校,北京:中华书局,1990年,第346页。
[28] 刘宝楠:《论语正义》,高流水点校,第130页。
[29] 刘宝楠:《论语正义》,高流水点校,第345页。
[30] 汉人韩婴《韩诗外传》卷五,亦载“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子”,最后一段“故孔子持文王之声,知文王之为人。师襄子曰:‘敢问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?’孔子曰:‘然。夫仁者好韦,和者好粉,智者好弹,有殷勤之意者好丽。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。’传曰:‘闻其末而达其本者,圣也’”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未见。参见韩婴:《韩诗外传集释》,许维遹校释,北京:中华书局,1980年,第176页。
[31] 朱熹: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第159页。
[32] 参见洪汉鼎:《论哲学诠释学的阐释概念》,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21年第7期。
[33] 何晏:《论语集解》,郑玄等注:《十三经古注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14年,第1961页。
[34] 洪汉鼎认为,阐释文本有三种类型,一是作者意图论,二是读者意义论,三是文本意义论。从哲学诠释学来说,我们只能接受文本意义论。参见洪汉鼎:《论哲学诠释学的阐释概念》,《中国社会科学》,2021年第7期。
[35] 朱熹: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第63页。
[36] 刘宝楠:《论语正义》,高流水点校,第34页。
| 【新澳好彩免费资料大全最新版本】 【澳门天天六开彩正版澳门】 |
| 【2024新澳门正版挂牌】 【新澳免费资料网站大全】 |
| 【2024新澳资料大全】 【澳彩资料免费的资料大全wwe】 |
| 【澳门必玩的三个景点】 【210期新澳天天开好彩结果】 |
| 【澳门最准最快的免费的】 【澳门天天彩全年正版资料】 |
| 【新澳2024年最新版资料】 【二四六澳门免费全全大全】 【奥门二四六天天免费好材料】 |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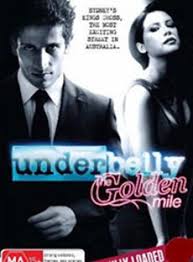
发表评论
阿尔夫·切森
9秒前:[12]所以,我们以“确认”一语来界定《孔子世家》中《风》《雅》《颂》的功能结构,以与《论语》中,孔子对“兴观群怨”思想结构的“确立”相区别。
IP:64.46.6.*
Sidko
1秒前:《孔子世家》的“四始说”,突出了儒家的人伦之道,明确把《诗》引向了政治教化与道德教化,这是汉代儒家诗学思想最为重要的特征。
IP:28.13.5.*
塔勒·比尔瑟尔
9秒前:硁硁乎!
IP:40.18.1.*
Voit
2秒前:由,譬使仁者而必信,安有伯夷、叔齐?
IP:84.26.5.*
荒川知佳
7秒前:这种价值依据并非《诗》之语言形态,而是《诗》之文本承载的道德观念,其中“礼”是最核心的价值观念。
IP:33.48.3.*